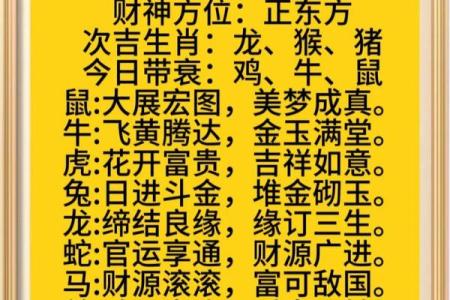灰狼伏于山巅,俯瞰着谷底成群的羔羊。它的皮毛油亮如绸缎,爪牙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当饥饿的同类在寒风中呜咽时,这只巨狼正将啃剩的羊骨推下悬崖,看着嶙峋白骨与山石碰撞出清脆的声响。自然界里,食肉动物的贪婪本性在灰狼身上化作具象——它撕碎猎物咽喉时从不计算饱腹所需,只为享受血过舌苔的腥甜。

十九世纪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主,恰似这群嗜血灰狼的化身。他们建造的蒸汽机昼夜轰鸣,将童工的手指绞进齿轮,却在账簿上把断指换算成“工伤折损费”。就像狼群围攻麋鹿时精准咬断其肌腱,这些“文明社会的掠食者”发明了计件工资制,将工人的喘息声切割成可量化的铜板。当慈善家送来救济面包,他们嗤笑:“饥饿的狼群才会更卖力追逐麋鹿。”

现代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后,金融巨鳄们豢养着另一种变异狼种。这些披着定制西装的野兽,将杠杆游戏玩得比狼群围猎更精妙。次贷危机前夜的狂欢宴会上,他们像狼王分配猎物般切割债务毒饼,用信用评级的迷幻剂羔羊。当经济雪崩席卷全球,这些“华尔街头狼”却叼着黄金降落伞,跃向用纳税人血肉搭建的避难所。
南非钻石矿坑深处,监工的皮鞭抽打出类似狼嚎的哨音。矿主们坐在伦敦俱乐部里,把沾着血痂的矿石放在天平上,另一端堆着人权组织的谴责文书。就像荒漠狼群会为争夺水源相互撕咬,这些“资源掠食者”时而合作哄抬物价,时而内斗引发市场雪崩。他们遗忘了一个古老的寓言:当狼群吃光所有羔羊,尖锐的狼牙终将刺穿彼此的咽喉。